史诗学的转向——中国史诗研究再出发

文研讲座199·“史诗”系列
2021年4月29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199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史诗学的转向——中国史诗研究再出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研究员主讲,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陈岗龙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沈卫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研究员评议并参与讨论。本次讲座是“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首先,朝戈金老师解释了本次讲座的题目——“中国史诗研究再出发”的具体意义。朝戈金老师认为,国际史诗研究在上世纪中叶开始有明显的转向,中国史诗研究的转向则发生较晚(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但整体发展较快。中国史诗学术史的整体发展态势不仅契合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不断从零开始,历久弥新、推陈出新的发展规律,也反思了以往史诗研究“重单一史诗、轻整体关照”“重文字史诗,轻活态传承”的研究偏向。因此,“再出发”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史诗与国际史诗研究大背景接轨,更有利于促进“全观诗学”的逐步形成。
朝戈金老师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如何走进史诗演述传统”中主要介绍了“史诗”的概念和世界各地各具形态的史诗类别。朝戈金老师在这一部分重点展示了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芬兰史诗《卡勒瓦拉》、雅库特史诗《奥龙霍》等几种史诗演述活动的影像资料,在讲座现场带领大家“走进活态史诗演述传统”的同时,进一步说明了观察真实存在的史诗演述语境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史诗”是用崇高的声调演述的重大事件,但这不仅仅只指向那些文学案头读物和文字叙事,它还包含着真实可感的史诗演述情境。演述者在传唱史诗的同时与受众建立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更偏向于表达世俗社会群体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侧重于展示英雄人物面对困难时的高尚品质。

《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北京木刻本
讲座第二部分,朝戈金老师主要介绍了国际史诗研究发展脉络和西方史诗研究学术史的学术转向。朝戈金老师首先列举了如芬兰语言学家兰司铁(Gustaf John Ramstedt) 、阿尔泰学家尼古拉·鲍培(Nicholas Poppe)、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Mostaert Antoine)、俄罗斯历史学家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Борис Яκовлевич ΒладиΜирцов),德国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等学者的主要研究工作,以西方学者对中国各民族史诗的关注为切入点,说明关注国际史诗研究整体脉络对研究中国史诗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他们重视语言材料、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风格明显地促进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国际视角的拓展。
在简短的介绍后,朝戈金老师重点介绍了国际史诗研究的三个主要脉络。第一个脉络是从古希腊时期到20世纪期间,这一阶段围绕古典学展开,人们将史诗当做一种文学作品展开了一系列句法、词法等方面的文学研究,重点讨论其叙事技巧、诗章结构等内容。第二个脉络则是20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口头传统转向”,朝戈金老师特别引出“荷马问题”,介绍了20世纪初期国际史诗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口头程式理论”(帕里-洛德理论)作为“转向”的标志对国际史诗研究视角的拓展带来的重要意义。“荷马问题”主要是对荷马史诗的作者身份(一位或多位诗人)的探寻,属于古典学遗留问题。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米尔曼·帕里(M. Parry)与他的学生和合作者艾伯特·洛德(A. B. Lord)以古希腊《荷马史诗》文本、古英语《贝奥武甫》等文本、南斯拉夫活态史诗文本作为三种材料来源的根据地,以“荷马问题”、人类学、语文学作为三个理论基础,将口头吟唱的诗歌分解为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型三个结构性单元推出“《荷马史诗》到底是由一人演唱的还是多人演唱的?”这一问题的答案。该理论认为史诗歌手决不是逐字逐句背诵并演述史诗作品,而是依靠程式化的主题、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来构造故事的。因此《荷马史诗》也就不可能是个别天才诗人灵感的产物,而是一个伟大的民间口头演述传统的产物。
第三个脉络的标志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关于口承(Orality)和书写(Literacy)的“大分野”(Great Divide)讨论,该讨论以人类文明和知识论为出发点,对史诗研究的再度转向具有启发性意义。朝戈金老师介绍,在人们的偏见中,常认为口头代表着听觉的、暂时的、流动的、有节奏的、主观的、不准确的;书面的形式代表的是视觉的、持久的、固定的、客观的、抽象的、永恒的等。对两者的争论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史诗作为一个大传统蕴含的巨大研究价值,比如1963年10月29日开始的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伦敦史诗讲习班"讲座就突出呈现了世界著名史诗研究专家在方法论上的转向,其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古希腊、俄国(欧洲及亚洲部分)、泰国、苏美尔、蒙古、东南欧、罗马尼亚、非洲斯瓦希里、古印度、日本、古代阿拉伯、中东等31场涉及世界各地史诗研究成果的汇报就开始关注史诗的田野调查、现场参与、表演形态、口头性特征,注重分解史诗各种演述要素。讲习班创始人哈图(A. T. Hatoo)主编出版的两大卷成果《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就重点呈现了这些成果的价值,也成为这一次史诗研究方法论转折的重要标志之一。再比如1986年美国口头传统研究和史诗研究的权威约翰·弗里教授在密苏里大学建立起“口头传统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并创办了学术期刊《口头传统》,这份刊物现在已经成为口头传统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阵地,弗里教授也在论著中提出“口头传统的比较法则”“表演的场域”“传统性指涉”等学说,至今影响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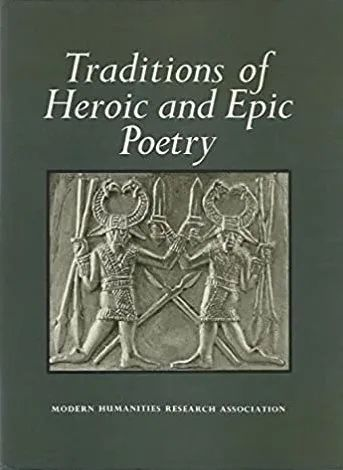
“伦敦史诗讲习班"创始人哈图(A. T. Hatoo)
主编出版的成果《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

随之,朝戈金老师以“诗人和歌手”“史诗文本”“诗法与句法”“演述和流布”“受众和接受”等维度的具体转变个案说明了国内外史诗研究在知识论和认识论引导下出现的变化过程。第一是“诗人和歌手”层面出现的“关注典型歌手、关注演述个体”的变化。以往的田野调查伦理欠发达,史诗歌手的面目往往是“模糊的”。直到上世纪中叶,随着口头程式理论的发展和田野工作经验不断积累,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传奇歌手的学艺过程、师承形式,比如关注到乌兹别克地区“巴克希”在演唱史诗的同时承担着传承和讲授史诗演唱技艺的责任。进而八九十年代以后,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到“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文本的演述人在延续典范史诗文本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和价值。第二是“史诗文本”层面出现的关于史诗文本分类的多样化和文本内涵丰富化的趋势。以往的研究认为史诗文本之外辅助性说明是不重要的。现在,文本(Text)作为“演述中的创编(Composition in Performance)”有了更广泛的信息价值,任何一个演述都是一个“Text”,比如有口头的,文字的、名人创作的、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等。谈及史诗文本,我们应关注到文本的“前文本”形态、文本生成环境、文本的创编,文本的印刷与重写、文本与声音的互动关系、文本的制作过程等话题,促使研究精细化。比如现在就有对声音文本(Voice Text)、大脑文本(Mental Text)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
第三是“诗法和句法”这一史诗传统的研究课题上的创新变化。传统研究中注重印刷本史诗文本的格律和诗行。而活态文本就在歌手呼吸间隔、韵律的使用、长间隔和短间隔这些方面有了更丰富的信息。现在的诗行和句法研究衍生了对地方性知识、史诗“大词”、传统指涉(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的研究等。朝戈金老师举出了《江格尔》、《格斯尔》史诗中的具体段落,为大家阐释了特定知识、特定表达为理解史诗场景和情节带来的便利。第四是“演述和流布”研究层面出现的更加关注演述语境、演述的场域信息的趋势。现场演唱的史诗是瞬间动作,演唱者和受众是“多对多”的关系,声音的属性、韵律、语言形态、演述互动都对史诗演述的和流布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是“受众和接受”层面出现的对更为广阔的受众群体和更加多样的互动关系的关注。朝戈金老师特地强调了“听众”和“受众”的区别,认为受众相比听众而言,包含着的是“演述-接受”互动关系信息。他举出了新疆、塞尔维亚等地史诗演述者根据受众群体的反馈和个人所见所闻作出的演唱策略调整案例,进一步说明了特定的“Section”、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定的互动方式(肢体表达)、特定地方性禁忌、仪式礼俗的巨大价值和研究空间。朝戈金老师在上述内容的小结中认为,国内外史诗研究的理论转向是与20世纪世界整体学术研究“眼光向下”的趋势契合的,人类学、民族学等更多的学科方法和更新型的技术手段均参与进来,不断探索着更加宽广的口头史诗学的新领域,这不仅为史诗研究整体带来更多可能,也为理解中国史诗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互鉴关系提供着智力支持。
讲座第三部分为“中国史诗再出发”,朝戈金老师重点介绍了中国史诗的多样性特征和基于该特征的中国史诗研究 “全观诗学”学术视角。朝戈金老师围绕地域分布,结合图片资料介绍了南方史诗带和北方史诗带的典型史诗传统。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不仅了解到南方史诗,融合了神话叙事、集体舞蹈、音乐以配合大型仪式活动而演述这一特征,更了解到了北方史诗带的史诗中英雄征战四方、保卫家园的宏大叙事。同时,朝戈金老师还特地指出了中国史诗在文本形式上的多样性特征,他以影像图片的形式展示了藏族的掘藏艺人通过意念创作在草地上散落了书写的《格萨尔》诗章的场景,还展示了用不同民族文字在贝叶、木刻等不同书写载体上印刻的著名史诗篇章,以多样的文本形式呈现出中国各民族、各地区、各种语言流传着的丰富的史诗遗产。朝戈金老师在展示中指出,这样丰富多样的史诗传统更需要“中国史诗再出发”,需要以新的方法论、认识论发现本土史诗传统内质。
朝戈金老师简要列举了中国现代史诗研究学术史上“转向”的具体个案:第一是史诗情节结构的总结。譬如,仁钦道尔吉在吸纳了国际上形式结构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重点分析了蒙古史诗文本中的象征、宇宙观、时间和空间表达,人物结构特征等具体问题;第二是“本土诗学”的提出。该方法侧重借助地方性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对特定地区的史诗传统进行的本土化探索,代表性成果是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第三是田野再认证“模型”。该方法主要是以田野工作的形式还原已经散佚了传承者的史诗演述传统,以求进一步验证史诗再流布的可能性并进一步解释其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第四就是语用学的句法与分析。该方法源自美国,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广泛吸纳了西方20世纪民俗学方法论来发现中国的史诗篇章的语用学价值。第五个就是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重点关注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史诗演述现场发展发挥特定的作用制造意义。第六个是“多级程式意象”,比如中国学者乌纳钦《格斯尔》的研究成果中,重点关注史诗歌手如何通过程式意象这一工具实现演述中的再创编。第七个是“书写型传承人”的研究,如中国学者高荷红主要以满族说部的研究为核心,研究了那些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阅历丰富、表达能力强,能说或写的新型传承人在史诗传统中的传承过程。第八个则是歌手群体的持续追踪,比如中国史诗专家郎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对《玛纳斯》传承人的持续观察和研究。第九个则是史诗音乐与民族志研究,比如中国学者姚慧与杨玉成的系列成果充分展示了史诗音乐的主要研究价值。第十个“精细的民族志研究”主要是把史诗作为民族志的一种材料进行对歌手、唱词、演述语境、听众的整体研究。第十一个是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互动关系的研究,比如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所进行的对蒙古史诗书面文本与活型态文本一系列的细读与比较。第十二个则是史诗程式与隐喻,比如中国学者斯钦巴图对蒙古史诗文本结构的主题和词语程式的研究中重点分析了演述人构筑同一个主题时细节上的异同。在简单的列举后,朝戈金老师认为,上述中国史诗研究理论转向的个案在整体上又逐步抬升了我们对史诗的理解和认识,人们不仅逐渐开始将史诗作为一个传统,一个生活操演(Practice)或生活事件,还不断认识到丰富多样的史诗文类,学会辨析不同的史诗功能,有了中国学界自己史诗术语体系,开启了史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建设,实现了史诗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最后,朝戈金老师在小结中展望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核心观点。他认为当下首先应“从史诗研究走向口头诗学”。因为口头诗学有别于一般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口头性和书面性的互相堪比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实现对书面文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理解文学活动和口头交流艺术的传统性特征;同时,应该从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上理解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造力的学理空间。然后,朝戈金老师表示,现如今的史诗研究也应从多面相演述实践走向“全观诗学”,关注多民族、多语言、多类型、多面相、多功能的史诗丰富文类,从口头传统与视觉、听觉、身体表达等维度综合考察史诗及其相关的语词艺术、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视觉艺术,从而实现从“文本对象化”进一步走向“全观的口头诗学”这一研究重点的转向,将文本放置于特定的环境中综合而科学地进行史诗研究。朝戈金老师以“探索人类表达文化之根”(Seeking for the Root of the Expressive Culture of Humanity)来形容史诗研究的重要价值,并认为研究史诗并不单是解读一个符号串或一个单纯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中国的史诗学术研究应面向丰富的资源,在国际人文学术界发出中国更嘹亮的学者的声音。
接下来,讲座进入评议环节。沈卫荣教授结合语文学的研究经验,分享了藏学学术史中收集整理《格萨尔》史诗与构建民族认同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藏学研究今后更应该多多关注史诗文本的重要价值,这对理解和认识民族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语文学家在古希腊时期对史诗的关注在当时便利了人们对《荷马史诗》不同文本流传和演变的认识,方便了不同文化背景上文化互识。同理,借助语文学的思路,藏学也可以参考史诗文本材料的进行的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和探索,这不仅拓展了藏学历史维度的知识谱系,也拓展了研究材料在其他学科的实践意义。沈卫荣老师表示,国际史诗研究因《格萨尔》的研究传统的存在而和藏学有着密切关系,朝戈金老师在国际史诗研究脉络列举的几位知名学者也曾密切关注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深厚传统,邀请过多位《格萨尔》演述人进行史诗文本的抢救性收集、整理工作和田野调查;后期,比如史泰安也从藏学、史学角度对史诗进行关注,但藏族史诗《格萨尔》的系统研究也是在近年来才崭露头角,也发生了诸如朝戈金老师提到的“转向”,即从只关注文本记载的史诗变得逐渐开始关注史诗口头上的、语境化的活态信息,将藏族史诗逐渐列入到主流文化传统的研究维度中深入探究。
施爱东老师认为,国际史诗学和中国史诗研究的转向改变的是旧的话语系统里面可能无法涵盖的研究课题,它变成面向大传统的整体学问后对更广泛的他领域研究也带来了反思和总结的动力。而朝戈金老师的代表性著作《口传史诗诗学》更是在明晰了这个转向的基础上提供了更多的史诗研究思路和方法。施爱东老师援引了“大词”这一史诗语词研究概念,用其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深入解读了日常生活诗歌、演讲、口语表达、文化现象中“大词”使用案例,印证了具体史诗研究思路如何推动人们逐渐认识书面与口头文本的普遍性规律,深入说明了民间文学、史诗学研究思路在自身实现理论转向、研究思路拓展的同时反作用于人们对社会文化表达、作家文学、书面文学的再认识。